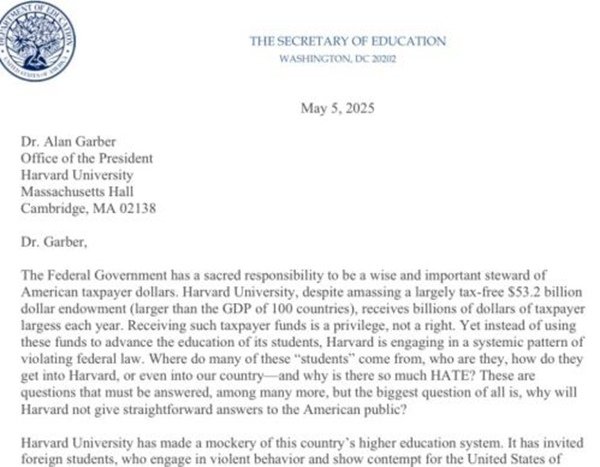广州博物馆正在热展的“人间镜像——广州汉晋墓葬的生命叙事”展览在线杠杆配资,以“镜”为媒,通过墓葬情况折射五彩斑斓的人间景象。今天咱们来聊聊这次展览中的铜镜,从方寸间读懂中国式生命智慧。
原始社会,人们要“照镜”,需要通过平整水面形成的倒影,才能照见自己的容颜。青铜时代的到来,人们铸造铜镜,作为祭祀仪式上的礼器。到汉代,打磨光滑的镜面,配上背面装饰的各类纹样或者字句的铜镜渐渐走下神坛,成为百姓生活的日用品,同时彰显主人的审美情趣、身份地位,甚至还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生命、宇宙的认识和理解。
展开剩余84%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齐家坪遗址M41号墓葬出土的铜镜
宇宙的解构——四神博局纹
博局纹镜是汉代最畅销的爆款铜镜,延续了近百年的时间,其主要特征是铺地花纹中间,规则装饰类似T、L、V字母状的纹饰。这么神秘的字母符号,有说很可能来源于木工使用的工具,V形符号称为规,它是用于画圆的工具。与T形正对的L形,称为矩,对应角尺,是木工刨方形木料时用来画线或者测量的工具。整个镜面呈现出来的效果规整划一。因此,这类博局镜也有另外一个名字“规矩镜”。这类的规矩镜往往装饰四神图案。该图案源于古代天文上的四象,即代表东、西、南、北四个方向的动物形象: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
镜钮周围有一双线方框,内有12个乳钉纹,间隔处刻篆书“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”十二地支铭文。它们不仅代表着时间的流转,更蕴含着万物生长与消亡的深刻哲理。远古时代,人们探寻天地人事的奥秘,依靠的就是天干地支。天干指天之道,代表空间;而地支则为地之道,象征时间,这两者相辅相成,形成一套联结时间和空间符号系统,影响人道的运行,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天、地、人的时空关系,也体现了古人原始朴素的宇宙观。
四神博局纹铜镜 东汉前期 广州博物馆藏
博局纹可能来源于汉代“桌游”
图左:六博棋盘,图自《战国至秦汉时期六博棋具研究》
图右: 博局纹人物画像镜 东汉 故宫博物院藏
对照上面的棋盘和铜镜纹饰,可以发现两者的线条走向几乎是一模一样。这完全有理由让我们相信,铜镜上的博局纹原型很可能来自汉代的桌游——六博棋。
汉代壁画中六博棋下棋的画面
六博棋,流行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,堪称世界上所有兵种盘局游戏的源头,例如象棋、国际象棋及将棋等,都由此逐步演化而来。游戏的棋盘设计为方形,表面阴刻规矩纹,并涂有红漆,画有四个圆点,寓意古老的八卦图。或许当时这种桌游深受玩家的喜爱,甚至棋盘的纹饰后来也被借用到了铜镜的装饰图案上。
马王堆六博棋具 湖南博物院藏
马王堆六博棋盘 湖南博物院藏
俗话说,“玩物不可丧志。”适当的娱乐可以增加情趣、放松身体。但是如果过分沉迷于娱乐,不仅丧志,更可能丧国。历史上就曾经发生过因六博棋引发的争斗,造成国与国之间的剑拔弩张。汉景帝刘启为太子的时候,酷爱六博游戏。一次吴王的太子到长安觐见,二人年龄相仿,于是相邀一起喝酒,玩“六博”。游戏间,吴王太子不慎言语激怒了汉景帝。盛怒之下,汉景帝拿起棋盘,失手打死了吴王太子。两国因此种下了仇恨的种子,为后来七国之乱也埋下伏笔。
六博游戏在汉武帝时期发展到了高峰,直到后来其他博弈游戏的出现,六博游戏的热度逐渐下降,到唐代最终推出历史舞台。
铜镜蕴含的文化内涵
铜镜作为一种贵重的随身物品,它不仅是日常用器,更是一种承载了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媒介。从纹饰、铭文、形制等方面都能反映出古人的生活状态,也记录时代的文化和艺术。
四神博局纹铜镜 东汉前期,
1957年西村皇帝岗41号墓出土
汉代继承战国时期对神仙思想的追求,通过星宿崇拜构建“天人合一”。前面提到的四神不仅是星宿崇拜的产物,还承载着汉代人对升仙的向往。同时,铜镜铭文上也往往配有诗文,表达对仙界生活、长生不老的渴求。广州博物馆藏四神博局纹铜镜环绕方框外围篆书刻诗句:“作佳镜哉真大好,上有仙人不知老。渴饮玉泉饥食枣,浮游天下傲四海。寿如金石为国保。”另一枚馆藏的汉代尚方铭规矩纹铜镜,上有诗文:“尚方作镜真大好,上有仙人不知老,渴饮玉泉饥食枣,浮游于天下敖四海,寿如金石兮。”此外,也有铜镜装饰同主题的简化版铭文,为“寿如金石”或者“寿如金石佳且好兮”等。
汉代人除了对个体健康长寿的期盼外,对家族子嗣的祝福和希冀同样也体现在铜镜上。“长宜子孙”是汉铜镜常见铭文,类似表述还有“宜君子孙”“宜子孙”等,都反映了希望家业能世代相传、子孙兴旺的愿望。
“长宜子孙”内向连弧纹铜镜 汉代 广州博物馆藏
铜镜从它作为祭祀品诞生的那天起在线杠杆配资,由最初宗教仪式和占卜活动用具到演变成为王公贵族的专属奢侈品,再到开始向民间普及,成为日用品,这一过程中见证了古人内心精神世界丰富多元的变化,也有助于认识古代社会的演变和进步。
发布于:北京市升阳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